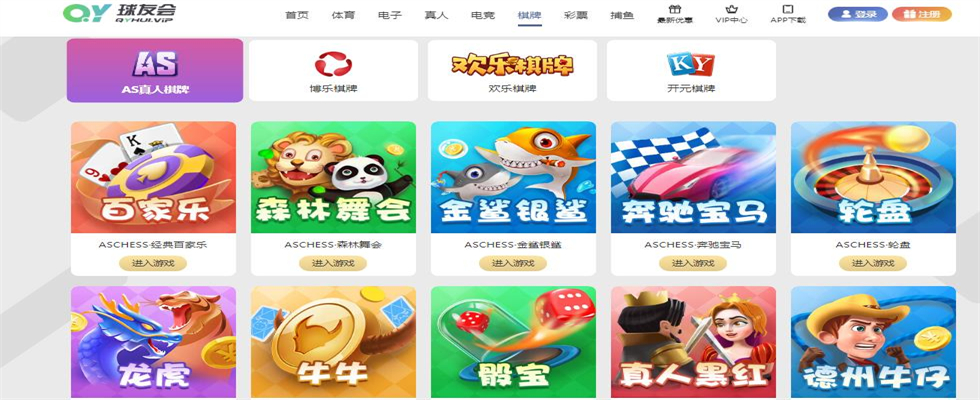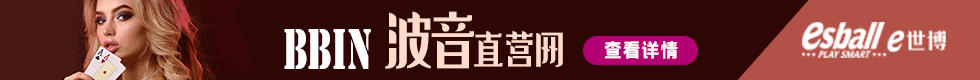哪些游戏会让人有深深的孤独感
发布日期:2022-04-01 08:02 点击次数:78
每一代GTA,当你完成所有能做的事情后,都会陷入强烈的孤独感。我曾经给GTA4写过一篇游戏小说,就是以孤独为主题(文长,图多来自网络)逃离自由城
 这件事一点都不难,真的。我将身体尽量放平,整个人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带着一丝慵懒与茫然。远处的海平面波光粼粼,如同洒过了一层昂贵的金粉,海鸥飞翔,波涛涌动,偶尔会有游艇一闪而过,切开金箔似的水面,在船尾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涟漪——尽管不可能闻到任何真正属于大海的味道,但这些场景仍旧使我有那么几个瞬间的感动。一架大客机划过蔚蓝的天空,摆动几下机翼,很快就消失在耀眼的阳光里。我眯起眼睛,默默地目送它离去。距离我身后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就是繁忙的Crockett大街。此时正值午后,车辆和行人川流不息,不时能够听到鸣笛与吵闹声,还有若隐若现的电台摇滚乐伴随着发动机轰鸣声飘过来。在沙滩上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三个黑人,他们穿着红色和绿色的运动装,远远地站在一起,低声谈论着什么。
这件事一点都不难,真的。我将身体尽量放平,整个人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带着一丝慵懒与茫然。远处的海平面波光粼粼,如同洒过了一层昂贵的金粉,海鸥飞翔,波涛涌动,偶尔会有游艇一闪而过,切开金箔似的水面,在船尾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涟漪——尽管不可能闻到任何真正属于大海的味道,但这些场景仍旧使我有那么几个瞬间的感动。一架大客机划过蔚蓝的天空,摆动几下机翼,很快就消失在耀眼的阳光里。我眯起眼睛,默默地目送它离去。距离我身后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就是繁忙的Crockett大街。此时正值午后,车辆和行人川流不息,不时能够听到鸣笛与吵闹声,还有若隐若现的电台摇滚乐伴随着发动机轰鸣声飘过来。在沙滩上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三个黑人,他们穿着红色和绿色的运动装,远远地站在一起,低声谈论着什么。
 又是一个惬意的下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我一直躺到夕阳西下,才缓缓站起身来,沿着沙滩上的木制廊桥走回到Crockett大街上。恰好一辆黄色的出租车驶过来。我站到路中间,出租车猛然刹住了车。我熟练地走到车旁,拉开车门,把里面的乘客粗暴地拽出来。那是个女人,她挣扎了几下就放弃了,骂了一句粗话,转身离去。我坐进了车里。“去Joliet街,走Duks Boulevard和东Borough高架桥。谢谢。”司机是个穿黄色马甲的老白人,他似乎完全不在意我赶走他的乘客,嘴里嘟囔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笑话,重新发动了车子。从Crockett街到我位于Joliet街住所的道路,有许多种选择。我通常喜欢先向西转到Oneida大道——那里有城里最好的散步便道——接着进入Montauk大道,一路可以欣赏街左侧Outlook公园里郁郁葱葱的橡树。然后我会路过士兵广场,那里总会有些傻瓜试图开车攀爬广场的水泥隔墩,撞得头破血流。接下来,车子从Dukes Boulevard北侧向转,直接上东Borough高架桥,沿途不仅可以看到海景,而且还有Charge岛上活力十足的大卡车相伴。最后我会在Bohan岛的Gainer街下高架,再开不到50米就到家了。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病态?但这是生存之道,至少是这座城市的生存之道。
又是一个惬意的下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我一直躺到夕阳西下,才缓缓站起身来,沿着沙滩上的木制廊桥走回到Crockett大街上。恰好一辆黄色的出租车驶过来。我站到路中间,出租车猛然刹住了车。我熟练地走到车旁,拉开车门,把里面的乘客粗暴地拽出来。那是个女人,她挣扎了几下就放弃了,骂了一句粗话,转身离去。我坐进了车里。“去Joliet街,走Duks Boulevard和东Borough高架桥。谢谢。”司机是个穿黄色马甲的老白人,他似乎完全不在意我赶走他的乘客,嘴里嘟囔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笑话,重新发动了车子。从Crockett街到我位于Joliet街住所的道路,有许多种选择。我通常喜欢先向西转到Oneida大道——那里有城里最好的散步便道——接着进入Montauk大道,一路可以欣赏街左侧Outlook公园里郁郁葱葱的橡树。然后我会路过士兵广场,那里总会有些傻瓜试图开车攀爬广场的水泥隔墩,撞得头破血流。接下来,车子从Dukes Boulevard北侧向转,直接上东Borough高架桥,沿途不仅可以看到海景,而且还有Charge岛上活力十足的大卡车相伴。最后我会在Bohan岛的Gainer街下高架,再开不到50米就到家了。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病态?但这是生存之道,至少是这座城市的生存之道。
 司机忠诚地遵照了我的指示,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我下了车,凑到驾驶室旁边,掏出手枪“砰”的一声,鲜血飞溅,司机整个身子都压在了方向盘上,喇叭声久久不停。我耸耸肩膀,把枪放回口袋。身后有一个疯子声嘶力竭地大吼着,于是我转过身去,狠狠地把他踹翻在地,用力地踩,直到他一动不动。做完这一切以后,我在附近的摊子里买了个热狗吃掉,用棒球棍打死摊主,然后回到自己家里,睡觉。自由城的一天结束了。
司机忠诚地遵照了我的指示,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我下了车,凑到驾驶室旁边,掏出手枪“砰”的一声,鲜血飞溅,司机整个身子都压在了方向盘上,喇叭声久久不停。我耸耸肩膀,把枪放回口袋。身后有一个疯子声嘶力竭地大吼着,于是我转过身去,狠狠地把他踹翻在地,用力地踩,直到他一动不动。做完这一切以后,我在附近的摊子里买了个热狗吃掉,用棒球棍打死摊主,然后回到自己家里,睡觉。自由城的一天结束了。
 所谓寂寞,究竟是什么呢?古往今来的哲人们给出了许多定义,也给出了许多描述。我想,没有人比我理解得更加深刻,因为没有人曾经身处我如今的环境。你可以想象,偌大的一个城市,里面充斥着数万辆汽车和数十万市民,可没有一个人真正拥有灵魂。在这些人背后,没有任何故事,也没有任何背景,他们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是随机出现在我附近,漫无目的地晃荡着——我甚至不确定在我视线之外,他们是否真的存在。没错,当我举枪要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惊恐,会抱头鼠窜,但那只是预设好的罢了。就算死了,也没有家庭为他们哭泣,也没有人会恨我。他们宛如行尸走肉一样在街上,目光呆滞,只会按照固定的几种模式做出反应。不光是人,就连整个城市都如同一具冰冷的机器,无比井然有序,无比冷漠。夜晚降临时路灯会按时点亮;城铁和地铁每天轰隆隆地在隧道里打转;高架桥的收费站横杆殷勤地抬上抬下;幸福女神像附近总是熙熙攘攘有许多游客;偶尔发生车祸,一分钟内疚会有救护车呜呜地出现在伤者身旁;弗朗西斯机场的航班起起落落,永远都那么繁忙。这些热闹的表象之下,是永远的一成不变,无比喧嚣却又无比寂寥。一个硕大的舞台布景,无数虚假的人体模型,我却生活其中。
所谓寂寞,究竟是什么呢?古往今来的哲人们给出了许多定义,也给出了许多描述。我想,没有人比我理解得更加深刻,因为没有人曾经身处我如今的环境。你可以想象,偌大的一个城市,里面充斥着数万辆汽车和数十万市民,可没有一个人真正拥有灵魂。在这些人背后,没有任何故事,也没有任何背景,他们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是随机出现在我附近,漫无目的地晃荡着——我甚至不确定在我视线之外,他们是否真的存在。没错,当我举枪要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惊恐,会抱头鼠窜,但那只是预设好的罢了。就算死了,也没有家庭为他们哭泣,也没有人会恨我。他们宛如行尸走肉一样在街上,目光呆滞,只会按照固定的几种模式做出反应。不光是人,就连整个城市都如同一具冰冷的机器,无比井然有序,无比冷漠。夜晚降临时路灯会按时点亮;城铁和地铁每天轰隆隆地在隧道里打转;高架桥的收费站横杆殷勤地抬上抬下;幸福女神像附近总是熙熙攘攘有许多游客;偶尔发生车祸,一分钟内疚会有救护车呜呜地出现在伤者身旁;弗朗西斯机场的航班起起落落,永远都那么繁忙。这些热闹的表象之下,是永远的一成不变,无比喧嚣却又无比寂寥。一个硕大的舞台布景,无数虚假的人体模型,我却生活其中。
 其实我并非一开始就生活其中。自由城对我来说,原本只是一个游戏罢了,不知何时开始我深陷其中——不是“沉迷深陷游戏”那种修辞手法,而是如字面意义般的深陷其中。究竟这是多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摸不清头脑。在自由城这种规律性极强、没有一点意外发生的地方,你很难去记住时间。电台广播和电视只能持续24小时,你唯一的选择是上网看看别人博客的更新来确定日子,但很快那些博客也都沉寂下来了。就算你想在墙壁上刻痕都没办法,自由城的东西除了建筑之外,都没办法持久。无论是落在地上的雨伞、汉堡、尸体、撞坏的汽车或者墙壁上的弹孔,都会很快消失,一切恢复如新。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并不属于这里,我应该属于一个比这里更丰富更混乱的世界。这点模糊的记忆是我的救命稻草,也是我的命中魔王。它让我满怀希望,也让我痛苦不堪。我最开始被困在自由城的时候,是兴奋。很快兴奋就变成了恐慌,恐慌变成了畏惧。周围有无数的人群,但只有自己是活生生的,这种感觉真的会要命。要命,这是一个修辞手法,一个笑话。事实上,我在自由城惟一的好处,或者说惟一的坏处是,我永远不会死。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从眼前一黑到站在医院门口那么一段短暂经历而已——无论我是被地铁撞死,从帝国大厦跳下来摔死或是被警察乱枪打死。最后一点自由,就这么被剥夺了,我连求死都不能。
其实我并非一开始就生活其中。自由城对我来说,原本只是一个游戏罢了,不知何时开始我深陷其中——不是“沉迷深陷游戏”那种修辞手法,而是如字面意义般的深陷其中。究竟这是多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摸不清头脑。在自由城这种规律性极强、没有一点意外发生的地方,你很难去记住时间。电台广播和电视只能持续24小时,你唯一的选择是上网看看别人博客的更新来确定日子,但很快那些博客也都沉寂下来了。就算你想在墙壁上刻痕都没办法,自由城的东西除了建筑之外,都没办法持久。无论是落在地上的雨伞、汉堡、尸体、撞坏的汽车或者墙壁上的弹孔,都会很快消失,一切恢复如新。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并不属于这里,我应该属于一个比这里更丰富更混乱的世界。这点模糊的记忆是我的救命稻草,也是我的命中魔王。它让我满怀希望,也让我痛苦不堪。我最开始被困在自由城的时候,是兴奋。很快兴奋就变成了恐慌,恐慌变成了畏惧。周围有无数的人群,但只有自己是活生生的,这种感觉真的会要命。要命,这是一个修辞手法,一个笑话。事实上,我在自由城惟一的好处,或者说惟一的坏处是,我永远不会死。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从眼前一黑到站在医院门口那么一段短暂经历而已——无论我是被地铁撞死,从帝国大厦跳下来摔死或是被警察乱枪打死。最后一点自由,就这么被剥夺了,我连求死都不能。
 我恍惚记得,曾经看过一部叫做《我是传奇》的电影。跟我相比,那部电影的男主角可幸运多了。他虽然孤孤单单一个人,可毕竟还有一条狗和危险的吸血鬼们为伴,生活孤独、危险,但绝不无聊。比危险更可怕的,就是无聊。无聊到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路都了然于胸,每一个行人的反应都不出所料,每一个电台的节目顺序都熟稔无比。自由城的细节是伟大的,但无论多么伟大的细节,也是有限的,无法真正模拟出人生本身,自然也就无法给予真正人生所特有的感受。我开始变着花样折磨自己,折磨着这个该死的城市。我开着直升机去撞幸福女神像,或者开到大街上,用旋翼尽量贴近地面,把行人高高卷起来;我打光了所有的鸽子,跳完了所有的跳跃点,赢得了每一个街区的赛车;我甚至试过去脱衣舞酒把对着那些丑陋的妓女自渎……所有规则允许或者规则不允许的事情,我都试了好几遍。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在自由城一样自由,也从来没有人像我一样被牢牢拘束。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你可以作任何事,但是没有任何用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才是最可怕的东西。说真的,我现在宁愿去和一个最卑微最苦难的人生去做交换,也不想呆在这个一成不变的安全囚笼。但这些事情我很快就厌烦了,于是我想逃离这个鬼地方。自由城是由四个大岛和数个小岛组成,四面环海,无边无际。我开着快艇朝着外海连续开了三、四天,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也试过攀上弗朗西斯机场的喷气式客机,可每次都跌落到跑道上,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打死。……现在的我,每天就是呆呆地靠在沙滩上,望着日出日落,然后打车回家,沿途偶尔会打死几个路人。我已经失去了做任何事的兴趣,长此以往,要么变成我家门前的疯子,要么变成行尸走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不必再担心。
我恍惚记得,曾经看过一部叫做《我是传奇》的电影。跟我相比,那部电影的男主角可幸运多了。他虽然孤孤单单一个人,可毕竟还有一条狗和危险的吸血鬼们为伴,生活孤独、危险,但绝不无聊。比危险更可怕的,就是无聊。无聊到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路都了然于胸,每一个行人的反应都不出所料,每一个电台的节目顺序都熟稔无比。自由城的细节是伟大的,但无论多么伟大的细节,也是有限的,无法真正模拟出人生本身,自然也就无法给予真正人生所特有的感受。我开始变着花样折磨自己,折磨着这个该死的城市。我开着直升机去撞幸福女神像,或者开到大街上,用旋翼尽量贴近地面,把行人高高卷起来;我打光了所有的鸽子,跳完了所有的跳跃点,赢得了每一个街区的赛车;我甚至试过去脱衣舞酒把对着那些丑陋的妓女自渎……所有规则允许或者规则不允许的事情,我都试了好几遍。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在自由城一样自由,也从来没有人像我一样被牢牢拘束。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你可以作任何事,但是没有任何用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才是最可怕的东西。说真的,我现在宁愿去和一个最卑微最苦难的人生去做交换,也不想呆在这个一成不变的安全囚笼。但这些事情我很快就厌烦了,于是我想逃离这个鬼地方。自由城是由四个大岛和数个小岛组成,四面环海,无边无际。我开着快艇朝着外海连续开了三、四天,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也试过攀上弗朗西斯机场的喷气式客机,可每次都跌落到跑道上,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打死。……现在的我,每天就是呆呆地靠在沙滩上,望着日出日落,然后打车回家,沿途偶尔会打死几个路人。我已经失去了做任何事的兴趣,长此以往,要么变成我家门前的疯子,要么变成行尸走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不必再担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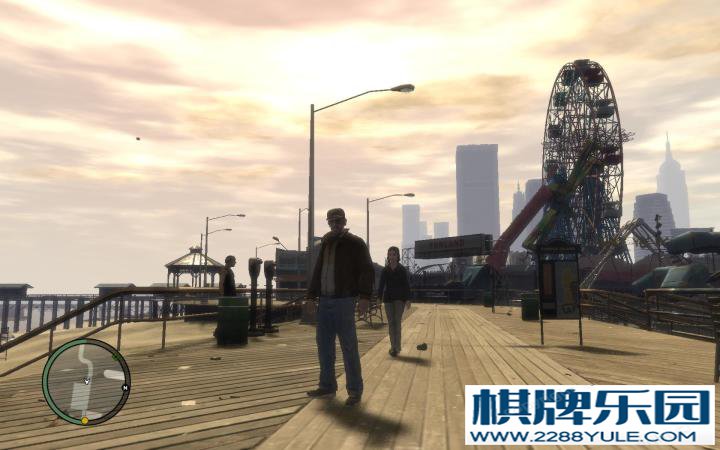
 这种生活在某一天——我无法确定是哪一天——发生了一点点改变。那一天早上,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出位于Albany大街的家门去,发觉有些不对劲。这座城市我太熟悉了,它的一举一动都瞒不了我。而今天我却觉出了一丝异常,也许是云层的流动,也许是车流的密度,也许是红绿灯变换的频率,说不清楚,总之就是不太一样。我随便在路上抢了一辆银灰色的SuperGT,沿着Albany大街一路向南开去,一直开到Algonquin岛的最南端。我心里很兴奋,“异常”是这个城市里最稀缺的东西,我暗自祈祷这千万不要是我的幻觉。
这种生活在某一天——我无法确定是哪一天——发生了一点点改变。那一天早上,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出位于Albany大街的家门去,发觉有些不对劲。这座城市我太熟悉了,它的一举一动都瞒不了我。而今天我却觉出了一丝异常,也许是云层的流动,也许是车流的密度,也许是红绿灯变换的频率,说不清楚,总之就是不太一样。我随便在路上抢了一辆银灰色的SuperGT,沿着Albany大街一路向南开去,一直开到Algonquin岛的最南端。我心里很兴奋,“异常”是这个城市里最稀缺的东西,我暗自祈祷这千万不要是我的幻觉。
 在Algonquin岛的东南角,有一个伸展到海面的观光直升机平台。我下车走过去,对着其中一架直升机开了一枪,驾驶员的血飞溅到玻璃上。然后我熟练地踢开尸体,坐到驾驶员的位置,直升机晃晃悠悠地飞起来,载着我朝整个自由城最高的建筑帝国大厦飞去。
在Algonquin岛的东南角,有一个伸展到海面的观光直升机平台。我下车走过去,对着其中一架直升机开了一枪,驾驶员的血飞溅到玻璃上。然后我熟练地踢开尸体,坐到驾驶员的位置,直升机晃晃悠悠地飞起来,载着我朝整个自由城最高的建筑帝国大厦飞去。
 当直升机慢慢接近帝国大厦顶端那巨大的天线时,我算准距离,猛然拉开门朝观光平台跳了下去,整个人恰好落在走道上,就地一滚,毫发无伤。失去控制的直升机,先是旋翼被天线塔撞断,然后整个机身翻滚着朝地面落下去,几秒钟后一阵低沉的爆炸声从下面传来。观光平台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这很平常,总会有几个随机出现的游客在附近晃荡——但这次不同,我落地以后,那个人直直朝我走来。他是个黑人,个子很高,看起来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注视我的眼神很坚定,自由城里的市民绝对无法做出这样目的性极其鲜明的举动。我的心脏开始狂跳。“你好,我等你很久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我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心理学因素罢了。”他耸耸肩,“当一个人感觉到不安定的时候,他总会选择一个可以最大限度掌控全局的地方呆着。整个自由城,只有帝国大厦可以俯瞰几乎整座城市。除此以来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你知道,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城市留下任何痕迹。”我们两个的目光同时朝外面转去,这里是自由城最高的地方,可以俯瞰差不多三分之二个城区,确实有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其实我更喜欢Crockett街的沙滩。”我老老实实回答。他大笑起来,然后比了个手势:“喝一杯去?”“好。”帝国大厦通向地面有一部电梯,但是我们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纵身跳下楼。周围的景物飞速闪过,然后我整个人高速撞到地面,眼前瞬间一片灰白颜色。在下一瞬间,我出现在Kunzite大街的医院前方,旁边步行过去几十米就是一间酒吧。
当直升机慢慢接近帝国大厦顶端那巨大的天线时,我算准距离,猛然拉开门朝观光平台跳了下去,整个人恰好落在走道上,就地一滚,毫发无伤。失去控制的直升机,先是旋翼被天线塔撞断,然后整个机身翻滚着朝地面落下去,几秒钟后一阵低沉的爆炸声从下面传来。观光平台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这很平常,总会有几个随机出现的游客在附近晃荡——但这次不同,我落地以后,那个人直直朝我走来。他是个黑人,个子很高,看起来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注视我的眼神很坚定,自由城里的市民绝对无法做出这样目的性极其鲜明的举动。我的心脏开始狂跳。“你好,我等你很久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我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心理学因素罢了。”他耸耸肩,“当一个人感觉到不安定的时候,他总会选择一个可以最大限度掌控全局的地方呆着。整个自由城,只有帝国大厦可以俯瞰几乎整座城市。除此以来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你知道,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城市留下任何痕迹。”我们两个的目光同时朝外面转去,这里是自由城最高的地方,可以俯瞰差不多三分之二个城区,确实有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其实我更喜欢Crockett街的沙滩。”我老老实实回答。他大笑起来,然后比了个手势:“喝一杯去?”“好。”帝国大厦通向地面有一部电梯,但是我们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纵身跳下楼。周围的景物飞速闪过,然后我整个人高速撞到地面,眼前瞬间一片灰白颜色。在下一瞬间,我出现在Kunzite大街的医院前方,旁边步行过去几十米就是一间酒吧。
 这是从帝国大厦到酒吧最快的办法,典型的自由城风格。我们两个都选择了这种方式,说明对于这个城市的了解都十分透彻。也许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被困在这里的可怜人。酒吧里没多少人,这里也没有真正的酒喝,只是我们习惯上觉得需要一种谈话的氛围。帝国大厦顶端的气氛太阴郁,不适合谈话。“你是怎么进来的?”我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出去。”他说,“这才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他的造型是一个与Little Jacob类似的黑人,不过双眼炯炯有神。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这的确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什么时候陷进自由城的,已经忘记了,我想你也是。不过我相信,我在自由城之前的生活里,从来没碰到过你,直到今天。我们也许原本身处两个一模一样但彼此独立的自由城,但因为某种原因,现在我们的世界合并了。”“我说为什么感觉城市有些不对劲呢,看来不是我过分敏感。”我自嘲道。黑人把身体朝前靠了靠,双手垫着下巴:“我还记得一点儿之前的事情。自由城应该属于某一个游戏的场景。在它的通常规则之下,整个城市只能容纳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也就是我们自己——现在两个城市合并成了一个,却拥有你我两个自由意志,这很奇怪。”“你是说,我们有机会出去?”我的呼吸骤然紧促。“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起变化了。”他说,露出宽慰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在自由城的人才能理解。变化,这是多么诱人的一个词啊。异常意味着变化,变化则意味着契机。我欣喜地点点头。“我是这么想的。那个游戏,除了通常规则以外,一定还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可以允许复数的自由意志同时出现。只要搞清楚这些特定规则,我们说不定就可以回去。”“那我们要怎么做?”我已经有些急不可待。“不知道。”黑人双手一摊。这让我有些失望,又有些惭愧。无论如何,他毕竟是在努力推测着真相,而我只知道浑浑噩噩地在沙滩上晒太阳,两下对比,我实在是太消极了。“但是一定有什么办法吧?”现在的我,就如同行将冻死之人看到远方的一簇火光,不知那是熊熊的篝火还是火星,但总归要凑近了去看一看才甘心。酒吧里陷入暂时的沉默。几个虚拟的市民从桌子旁走开,其中一个醉得不醒人事,他们对我们熟视无睹,跌跌撞撞的走出门去,然后凭空消失在空气中。黑人抓起一个飞镖,朝靶盘丢过去,准确地刺中了靶心。然后我们轮流投掷,最后我以三分之差赢得了比赛。“你是否还记得从前的世界?”黑人突然问道。我摇摇头:“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的印象——准确地说,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与自由城不同’这件事本身,至于如何不同,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我猜,这也许就是我们困在自由城的原因。”黑人搓响手指,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自由意志这种东西,需要记忆作为基础。人生过往的一点一滴,都是构成我们追求自由的源动力。”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而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正在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逐渐消磨掉以往的记忆。我们会痛苦,会愤怒,是因为我们仍旧怀着对从前生活的渴望。当我们彻底忘掉之前的一切时,这个城市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完全融进去,变得和他们一样。”他指了指酒吧老板,老板正面无表情地站在吧台后。就算我们用枪或者棒球棒把他打死,他也不会产生任何情绪波动。我觉得后背一阵发凉,这正是近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写照:彻底放弃了思考与挣扎,每天只是躺在沙滩上看太阳,让脑子变得麻木。按照黑人的说法,我正滑向不可逆转的深渊,整个自由城像怪兽一样长开漆黑的大嘴,等待着我掉进去。“这可真是……太可怕了。”我嗫嚅道,同时擦了擦额头并不存在的冷汗。黑人宽慰地笑了笑,比了一个放心的手势:“事情还没糟糕到那个程度。你看,我们不是碰到对方了么?如果我的理论没错的话,自由城靠吸取我们的记忆来吞噬我们,那么反过来想,只要我们恢复了记忆,那么就有希望从这里逃离。”我精神一振,随即又问道:“要怎么恢复?”“至少我们都记得,这里本来属于一个游戏的场景。”黑人道,“这个城市我确信是按照现实世界搭建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按照黑人的说法,记忆的回复需要一种叫做联想法的手段。这种手法的重点,是从一个确实的回忆点出发,通过不断联想回忆起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的回忆很确定自由城本来是一个游戏场景,那么游戏又是什么?应该是一种交互式的程序。程序是什么?似乎可以在电脑或者某种机器上运行;电脑是在哪里发明的?美国。美国是在哪里?是在美洲;在那个世界除了美洲还有什么洲?我能数出两个,黑人能数出三个……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事实上,正如黑人预料的,自由城就是现实某个城市的投影,我怀着联想的目的去搜寻,发现周围到处都是记忆起点。我能从路上的黄色出租车联想到撒哈拉沙漠;能从Booth隧道联想到飞翔在地球上空的GPS卫星网;从Alderney国家监狱联想到《肖申克的赎罪》以及好莱坞。我找到了在自由城的生存意义,并且乐此不疲。麻木的大脑,就象是久未润滑的老滑轮,开始吱吱扭扭地转动起来。我回想起了许多东西,回忆起来的生活细节越多,想脱离自由城的心愿就越强烈。这一天,我来到Tinderbox街的脱衣酒吧里,等着黑人过来。自从确定了联想恢复记忆的战略之后,我们白天各自行动,去寻找自己熟悉的记忆点,然后在太阳落山后来到这里的酒吧碰头,分享自己的联想成果。这里是自由城最热闹的地方,喧嚣的人群和舞动的脱衣舞女比别处更有生气。天色擦黑的时候,一辆橙色的跑车停到脱衣酒吧前面,黑人从车里走出来。我发现他的脸色并不算好,心里想在自由城这种鬼地方,还能有什么发愁的事?就我目前回复的记忆里,黑人是我见过最有智慧的人。在我坐困愁城的时候,他已经用敏锐的眼光与思维发掘出一条回归之路,并且毫不迟疑地执行。这样一个人,难道也碰到不能解决的事情了?“你来了?”我靠在沙发里,冲他懒洋洋地挥了挥手。黑人没有理睬主动迎上去的妓女,径直走到我旁边。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不再坚定,在我和舞台之间反复游离。“我想起来一些事情。”他的声音很干瘪。“我们不是每天都想起一些事情嘛。”我试图宽慰他,“你今天想起来什么东西了?Lady Gaga,还是大熊猫?”黑人没有回答,而是举起枪来对准了我。他端起来的是一把AK47,枪口对着我的太阳穴。“嗯?”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这个举动的含义。在自由城,拿枪对准别人并不是一件很冒犯的事,因为我们永生不死。他就算开枪,也最多是把我送到三个街区以外的Edison医院罢了。“Just Kidding,Sorry。”他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开了枪。我的身子一下子从沙发歪斜斜地倒下去,周围变得黑白一片,下一个瞬间,我已站在Edison医院门口。我对黑人的举动迷惑不解,互相开枪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总得有个理由,而且为何他面露愧疚,显得十分犹豫呢?很快我又在Colony小岛碰到了他。我问他,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等到回答,因为他二话不说,掏出枪来就把我直接毙掉了。满腹疑云的我想,难道这也是回忆计划的一部分么?通过对同伴开枪来回忆现实社会里的凶杀与犯罪?我决心一定得弄个明白。黑人是我尊敬的人,也是我钦佩的人,即使我们永生,被自己尊敬的人连续两次杀死也不是件愉快的事。第三次,我正站在Broker城区的某一个城铁站台上,城铁轰隆隆地开进站里,忽然一支手枪从后面顶住了我。“是你吗?”我不动声色。“我别无选择。”黑人的声音充满了困惑与痛苦。“那么我也是。”站台上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在他拿枪对准我的时候,我已经把一枚手雷拔出了引信,然后丢到脚面。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高高地飞在半空,然后落在地上。这一次很巧,我们出现在同一家医院门口。我们同时拔枪,对准了对方。“这么说你也想起来了?”黑人问,表情里既有恐惧,也有解脱。“我已经被杀死两次了,怎么也该想起来了,这都要拜你的联想法所赐。”我说,同时把准星对准了他的头部,“说真的,我实在不想对你开枪,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伙伴。如果没有你,我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刚才不是说了么,我们别无选择。”这一次传来两声枪响。唯一不同的是,我手里端的是AK47,而他的是手枪。在自由城的世界里,AK47比手枪的射速与杀伤力都大得多。于是,我看到黑人的身躯轰然倒地,还微微抽搐。他没有再度出现在医院前,可能是被传送到其他岛上去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他这个举动的含义了。自由城的那个游戏,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机模式,每一个城市只能拥有一个自由意志;还有一种网络模式,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叫做死亡竞赛。在这种模式中,不同玩家可以通过网络置身于同一片城区,以杀死对方的次数作为计数,先够50次的人就是胜利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同一个城市才能出现复数自由意志。黑人在第一次杀死我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回忆起这个细节了,难怪他那么愧疚。在被他杀死两次以后,遭背叛的痛苦和愤怒也让我这部分的记忆复苏。这真讽刺,我们拼命回忆人生,最终的结果却是让我们兵戎相见。当黑人出现在我的城市时——或者说我出现在黑人的城市——其实这个模式就已经启动了。这是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死亡竞赛。和解是不可能的,胜利者只允许有一个人。即使我们轮流向对方开枪,总有一个人先到50次,另外一个人必然失败。用火箭筒或者手雷同归于尽这种事,是不被承认的,一定要确实地杀死对方并且自己存活下来,才能够算数。所以棋牌资讯当我回复这一部分记忆之后,我意识到,我与黑人之间的战斗不可避免。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就算你好不容易成功地杀死一次,死去的人,会随机出现在三家医院之一的门前,杀手无法立刻赶到。这可以给予被杀死者可以反攻的机会。不会发生杀手在复活点堵门连杀的事情。雷达为我们提供了对方在地图上的大概位置,没有更多细节。这意味着这场决斗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在是有些讽刺。在这个自由城里,唯一两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却要拔枪相向。但无论如何,我想出去,因此只能鼓起勇气,与我唯一的同伴交手。目前黑人已经杀死了我两次,我杀死他一次。2比1。接下来,就要看谁对这座城市更熟悉了。我抢了一辆车,直接驱车前往唐人街。那里有一个枪械店,里面卖各种枪械、子弹和防弹背心,我现在必须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车子快接近Columbus大街与Emerald路口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从狭窄管道里高速喷出的声音,是火箭筒!
这是从帝国大厦到酒吧最快的办法,典型的自由城风格。我们两个都选择了这种方式,说明对于这个城市的了解都十分透彻。也许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被困在这里的可怜人。酒吧里没多少人,这里也没有真正的酒喝,只是我们习惯上觉得需要一种谈话的氛围。帝国大厦顶端的气氛太阴郁,不适合谈话。“你是怎么进来的?”我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出去。”他说,“这才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他的造型是一个与Little Jacob类似的黑人,不过双眼炯炯有神。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这的确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什么时候陷进自由城的,已经忘记了,我想你也是。不过我相信,我在自由城之前的生活里,从来没碰到过你,直到今天。我们也许原本身处两个一模一样但彼此独立的自由城,但因为某种原因,现在我们的世界合并了。”“我说为什么感觉城市有些不对劲呢,看来不是我过分敏感。”我自嘲道。黑人把身体朝前靠了靠,双手垫着下巴:“我还记得一点儿之前的事情。自由城应该属于某一个游戏的场景。在它的通常规则之下,整个城市只能容纳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也就是我们自己——现在两个城市合并成了一个,却拥有你我两个自由意志,这很奇怪。”“你是说,我们有机会出去?”我的呼吸骤然紧促。“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起变化了。”他说,露出宽慰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在自由城的人才能理解。变化,这是多么诱人的一个词啊。异常意味着变化,变化则意味着契机。我欣喜地点点头。“我是这么想的。那个游戏,除了通常规则以外,一定还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可以允许复数的自由意志同时出现。只要搞清楚这些特定规则,我们说不定就可以回去。”“那我们要怎么做?”我已经有些急不可待。“不知道。”黑人双手一摊。这让我有些失望,又有些惭愧。无论如何,他毕竟是在努力推测着真相,而我只知道浑浑噩噩地在沙滩上晒太阳,两下对比,我实在是太消极了。“但是一定有什么办法吧?”现在的我,就如同行将冻死之人看到远方的一簇火光,不知那是熊熊的篝火还是火星,但总归要凑近了去看一看才甘心。酒吧里陷入暂时的沉默。几个虚拟的市民从桌子旁走开,其中一个醉得不醒人事,他们对我们熟视无睹,跌跌撞撞的走出门去,然后凭空消失在空气中。黑人抓起一个飞镖,朝靶盘丢过去,准确地刺中了靶心。然后我们轮流投掷,最后我以三分之差赢得了比赛。“你是否还记得从前的世界?”黑人突然问道。我摇摇头:“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的印象——准确地说,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与自由城不同’这件事本身,至于如何不同,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我猜,这也许就是我们困在自由城的原因。”黑人搓响手指,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自由意志这种东西,需要记忆作为基础。人生过往的一点一滴,都是构成我们追求自由的源动力。”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而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正在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逐渐消磨掉以往的记忆。我们会痛苦,会愤怒,是因为我们仍旧怀着对从前生活的渴望。当我们彻底忘掉之前的一切时,这个城市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完全融进去,变得和他们一样。”他指了指酒吧老板,老板正面无表情地站在吧台后。就算我们用枪或者棒球棒把他打死,他也不会产生任何情绪波动。我觉得后背一阵发凉,这正是近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写照:彻底放弃了思考与挣扎,每天只是躺在沙滩上看太阳,让脑子变得麻木。按照黑人的说法,我正滑向不可逆转的深渊,整个自由城像怪兽一样长开漆黑的大嘴,等待着我掉进去。“这可真是……太可怕了。”我嗫嚅道,同时擦了擦额头并不存在的冷汗。黑人宽慰地笑了笑,比了一个放心的手势:“事情还没糟糕到那个程度。你看,我们不是碰到对方了么?如果我的理论没错的话,自由城靠吸取我们的记忆来吞噬我们,那么反过来想,只要我们恢复了记忆,那么就有希望从这里逃离。”我精神一振,随即又问道:“要怎么恢复?”“至少我们都记得,这里本来属于一个游戏的场景。”黑人道,“这个城市我确信是按照现实世界搭建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按照黑人的说法,记忆的回复需要一种叫做联想法的手段。这种手法的重点,是从一个确实的回忆点出发,通过不断联想回忆起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的回忆很确定自由城本来是一个游戏场景,那么游戏又是什么?应该是一种交互式的程序。程序是什么?似乎可以在电脑或者某种机器上运行;电脑是在哪里发明的?美国。美国是在哪里?是在美洲;在那个世界除了美洲还有什么洲?我能数出两个,黑人能数出三个……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事实上,正如黑人预料的,自由城就是现实某个城市的投影,我怀着联想的目的去搜寻,发现周围到处都是记忆起点。我能从路上的黄色出租车联想到撒哈拉沙漠;能从Booth隧道联想到飞翔在地球上空的GPS卫星网;从Alderney国家监狱联想到《肖申克的赎罪》以及好莱坞。我找到了在自由城的生存意义,并且乐此不疲。麻木的大脑,就象是久未润滑的老滑轮,开始吱吱扭扭地转动起来。我回想起了许多东西,回忆起来的生活细节越多,想脱离自由城的心愿就越强烈。这一天,我来到Tinderbox街的脱衣酒吧里,等着黑人过来。自从确定了联想恢复记忆的战略之后,我们白天各自行动,去寻找自己熟悉的记忆点,然后在太阳落山后来到这里的酒吧碰头,分享自己的联想成果。这里是自由城最热闹的地方,喧嚣的人群和舞动的脱衣舞女比别处更有生气。天色擦黑的时候,一辆橙色的跑车停到脱衣酒吧前面,黑人从车里走出来。我发现他的脸色并不算好,心里想在自由城这种鬼地方,还能有什么发愁的事?就我目前回复的记忆里,黑人是我见过最有智慧的人。在我坐困愁城的时候,他已经用敏锐的眼光与思维发掘出一条回归之路,并且毫不迟疑地执行。这样一个人,难道也碰到不能解决的事情了?“你来了?”我靠在沙发里,冲他懒洋洋地挥了挥手。黑人没有理睬主动迎上去的妓女,径直走到我旁边。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不再坚定,在我和舞台之间反复游离。“我想起来一些事情。”他的声音很干瘪。“我们不是每天都想起一些事情嘛。”我试图宽慰他,“你今天想起来什么东西了?Lady Gaga,还是大熊猫?”黑人没有回答,而是举起枪来对准了我。他端起来的是一把AK47,枪口对着我的太阳穴。“嗯?”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这个举动的含义。在自由城,拿枪对准别人并不是一件很冒犯的事,因为我们永生不死。他就算开枪,也最多是把我送到三个街区以外的Edison医院罢了。“Just Kidding,Sorry。”他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开了枪。我的身子一下子从沙发歪斜斜地倒下去,周围变得黑白一片,下一个瞬间,我已站在Edison医院门口。我对黑人的举动迷惑不解,互相开枪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总得有个理由,而且为何他面露愧疚,显得十分犹豫呢?很快我又在Colony小岛碰到了他。我问他,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等到回答,因为他二话不说,掏出枪来就把我直接毙掉了。满腹疑云的我想,难道这也是回忆计划的一部分么?通过对同伴开枪来回忆现实社会里的凶杀与犯罪?我决心一定得弄个明白。黑人是我尊敬的人,也是我钦佩的人,即使我们永生,被自己尊敬的人连续两次杀死也不是件愉快的事。第三次,我正站在Broker城区的某一个城铁站台上,城铁轰隆隆地开进站里,忽然一支手枪从后面顶住了我。“是你吗?”我不动声色。“我别无选择。”黑人的声音充满了困惑与痛苦。“那么我也是。”站台上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在他拿枪对准我的时候,我已经把一枚手雷拔出了引信,然后丢到脚面。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高高地飞在半空,然后落在地上。这一次很巧,我们出现在同一家医院门口。我们同时拔枪,对准了对方。“这么说你也想起来了?”黑人问,表情里既有恐惧,也有解脱。“我已经被杀死两次了,怎么也该想起来了,这都要拜你的联想法所赐。”我说,同时把准星对准了他的头部,“说真的,我实在不想对你开枪,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伙伴。如果没有你,我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刚才不是说了么,我们别无选择。”这一次传来两声枪响。唯一不同的是,我手里端的是AK47,而他的是手枪。在自由城的世界里,AK47比手枪的射速与杀伤力都大得多。于是,我看到黑人的身躯轰然倒地,还微微抽搐。他没有再度出现在医院前,可能是被传送到其他岛上去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他这个举动的含义了。自由城的那个游戏,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机模式,每一个城市只能拥有一个自由意志;还有一种网络模式,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叫做死亡竞赛。在这种模式中,不同玩家可以通过网络置身于同一片城区,以杀死对方的次数作为计数,先够50次的人就是胜利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同一个城市才能出现复数自由意志。黑人在第一次杀死我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回忆起这个细节了,难怪他那么愧疚。在被他杀死两次以后,遭背叛的痛苦和愤怒也让我这部分的记忆复苏。这真讽刺,我们拼命回忆人生,最终的结果却是让我们兵戎相见。当黑人出现在我的城市时——或者说我出现在黑人的城市——其实这个模式就已经启动了。这是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死亡竞赛。和解是不可能的,胜利者只允许有一个人。即使我们轮流向对方开枪,总有一个人先到50次,另外一个人必然失败。用火箭筒或者手雷同归于尽这种事,是不被承认的,一定要确实地杀死对方并且自己存活下来,才能够算数。所以棋牌资讯当我回复这一部分记忆之后,我意识到,我与黑人之间的战斗不可避免。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就算你好不容易成功地杀死一次,死去的人,会随机出现在三家医院之一的门前,杀手无法立刻赶到。这可以给予被杀死者可以反攻的机会。不会发生杀手在复活点堵门连杀的事情。雷达为我们提供了对方在地图上的大概位置,没有更多细节。这意味着这场决斗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在是有些讽刺。在这个自由城里,唯一两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却要拔枪相向。但无论如何,我想出去,因此只能鼓起勇气,与我唯一的同伴交手。目前黑人已经杀死了我两次,我杀死他一次。2比1。接下来,就要看谁对这座城市更熟悉了。我抢了一辆车,直接驱车前往唐人街。那里有一个枪械店,里面卖各种枪械、子弹和防弹背心,我现在必须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车子快接近Columbus大街与Emerald路口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从狭窄管道里高速喷出的声音,是火箭筒!
 我下意识地拉开车门,从车子里跳了出去。下一瞬间,车子变成了一个大火球。我滚落到人行道上,血格一下子掉了大半。街道上的车子都停下来,还有人在尖叫。我看到一个小黑影从天空飞过来,划过一条弧线落在离我不远的地面。我别无选择,只能跳到路中间。手雷爆炸的同时,远处传来炒豆般的噼啪声。我一下子被数十枚子弹刺穿,当即倒在地上。一次极其漂亮的伏击。黑人预料到我会前往枪械店补充武器,他早早就驾驶直升机飞到附近街口的楼房顶上。他连续用火箭筒和手雷,逼迫我离开人行道,来到没有任何遮蔽的十字路口,然后居高临下用M16把我打成筛子。3比1。我这次选择了打车,这是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我到了South Parkway南侧的那一片大工地,那里有一片高耸入云的塔吊。我飞快地爬上最高的那一台,拿出狙击枪。这么作风险很大,因为如果他对这一片区域足够熟悉的话,就会格外留意高处的塔吊。我们两个人对狙的话,在塔吊上的我比他更容易被击中。但我愿意赌上一把。
我下意识地拉开车门,从车子里跳了出去。下一瞬间,车子变成了一个大火球。我滚落到人行道上,血格一下子掉了大半。街道上的车子都停下来,还有人在尖叫。我看到一个小黑影从天空飞过来,划过一条弧线落在离我不远的地面。我别无选择,只能跳到路中间。手雷爆炸的同时,远处传来炒豆般的噼啪声。我一下子被数十枚子弹刺穿,当即倒在地上。一次极其漂亮的伏击。黑人预料到我会前往枪械店补充武器,他早早就驾驶直升机飞到附近街口的楼房顶上。他连续用火箭筒和手雷,逼迫我离开人行道,来到没有任何遮蔽的十字路口,然后居高临下用M16把我打成筛子。3比1。我这次选择了打车,这是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我到了South Parkway南侧的那一片大工地,那里有一片高耸入云的塔吊。我飞快地爬上最高的那一台,拿出狙击枪。这么作风险很大,因为如果他对这一片区域足够熟悉的话,就会格外留意高处的塔吊。我们两个人对狙的话,在塔吊上的我比他更容易被击中。但我愿意赌上一把。
 雷达里很快出现一个红点。他一定在雷达里也看到我了。但雷达只能显示出粗略的位置,而无法精确定位,这是我的机会。一辆悍马从South Parkway开过来,黑人把车开的很慢,试图混在NPC的车队里鱼目混珠,可惜还是被我一眼认出来——NPC车辆始终保持匀速,而悍马却是忽快忽慢,很显眼——他很狡猾,悍马的防御力很高,很难用狙击枪从远处射穿。不过反过来说,他也无法第一时间进入狙击站位。我开了第一枪,击中了悍马前方一辆小面包的后轮。小面包骤然停下来,司机惊慌地逃出来。悍马没有停住,反而开始加速朝前冲去。悍马的强大马力一下子把面包车推开。看来黑人从小面包中枪的一瞬间,就意识到我已经占得了狙击先机,他如果继续慢悠悠地前进,就会给我提供一个瞄准驾驶室的机会。他做出了正确判断,加大油门,试图利用悍马的厚装甲飞速逃离这个区域,悍马撞开小面包以后,凶悍地朝Denver大道转去。只要他再前进三十米,Denver大道两侧的高层建筑就能为他提供最完美的掩护。可惜这时候已经晚了。我开了第二枪,仍旧没有瞄准悍马,而是对准了在Denver大道和South Parkway交汇处的一辆油罐车。这是我一开始就故意停在那里的,是我送给黑人的小礼物。子弹击中油罐车的瞬间,发生了极其剧烈的爆炸,火焰和暴风将刚好路过的悍马也卷了进去。自由城和现实不同,你停好的一辆车,如果离开你的视线,车子就会很快消失。所以黑人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利用其他车辆来做埋伏。事实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处既是黑人逃跑的必经之路,又在我视线范围之内的位置。3比2。我收起枪,飞快地爬下塔台,黑人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的。在接下来的三天内,整个城市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战场。说来讽刺,这种激烈的交锋与其说是为了脱离自由城,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无聊。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我大脑运转速度极快,长久的锈蚀与麻木一扫而空。我在战争中恢复了以往的敏锐与想象力,记忆恢复前所未有的快。我不再长吁短叹伤春悲秋,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杀死黑人以及如何防止被他杀死。我在弗朗西斯机场和Drill街的断桥各自杀了黑人一次;黑人则在中央公园和Alderney的废弃工厂回以颜色。我在高耸入云的大厦之间击落了黑人的直升机,然后他就打爆了我在海面划S的快艇。我们甚至在中央岛屿的地铁隧道里展开了一场极其华丽的追逐战,我们骑的都是摩托车,在漆黑的隧道里围着Algonquin岛转了大半圈,最后谁也没赢。我们一起被迎面而来的地铁撞死,
雷达里很快出现一个红点。他一定在雷达里也看到我了。但雷达只能显示出粗略的位置,而无法精确定位,这是我的机会。一辆悍马从South Parkway开过来,黑人把车开的很慢,试图混在NPC的车队里鱼目混珠,可惜还是被我一眼认出来——NPC车辆始终保持匀速,而悍马却是忽快忽慢,很显眼——他很狡猾,悍马的防御力很高,很难用狙击枪从远处射穿。不过反过来说,他也无法第一时间进入狙击站位。我开了第一枪,击中了悍马前方一辆小面包的后轮。小面包骤然停下来,司机惊慌地逃出来。悍马没有停住,反而开始加速朝前冲去。悍马的强大马力一下子把面包车推开。看来黑人从小面包中枪的一瞬间,就意识到我已经占得了狙击先机,他如果继续慢悠悠地前进,就会给我提供一个瞄准驾驶室的机会。他做出了正确判断,加大油门,试图利用悍马的厚装甲飞速逃离这个区域,悍马撞开小面包以后,凶悍地朝Denver大道转去。只要他再前进三十米,Denver大道两侧的高层建筑就能为他提供最完美的掩护。可惜这时候已经晚了。我开了第二枪,仍旧没有瞄准悍马,而是对准了在Denver大道和South Parkway交汇处的一辆油罐车。这是我一开始就故意停在那里的,是我送给黑人的小礼物。子弹击中油罐车的瞬间,发生了极其剧烈的爆炸,火焰和暴风将刚好路过的悍马也卷了进去。自由城和现实不同,你停好的一辆车,如果离开你的视线,车子就会很快消失。所以黑人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利用其他车辆来做埋伏。事实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处既是黑人逃跑的必经之路,又在我视线范围之内的位置。3比2。我收起枪,飞快地爬下塔台,黑人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的。在接下来的三天内,整个城市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战场。说来讽刺,这种激烈的交锋与其说是为了脱离自由城,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无聊。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我大脑运转速度极快,长久的锈蚀与麻木一扫而空。我在战争中恢复了以往的敏锐与想象力,记忆恢复前所未有的快。我不再长吁短叹伤春悲秋,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杀死黑人以及如何防止被他杀死。我在弗朗西斯机场和Drill街的断桥各自杀了黑人一次;黑人则在中央公园和Alderney的废弃工厂回以颜色。我在高耸入云的大厦之间击落了黑人的直升机,然后他就打爆了我在海面划S的快艇。我们甚至在中央岛屿的地铁隧道里展开了一场极其华丽的追逐战,我们骑的都是摩托车,在漆黑的隧道里围着Algonquin岛转了大半圈,最后谁也没赢。我们一起被迎面而来的地铁撞死,
 日起日落,比分在不断上升。我们疯狂地杀死对方,只为自己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中的一次对决中,我成功地把他逼入了死角,然后用枪顶住了他的头。我对他说:“你也无法确认,杀死对方五十次后,就一定可以脱离这座城市吧?”黑人点了点头:“这不过是一个猜想。”我忽生感慨:“也就是说我们正在为一个虚无缥缈不能确定的玩意儿大打出手,这可真讽刺。”黑人笑了:“那么你会因此而放下枪吗?”“不会,这可真悲哀。”我回答。黑人耸耸肩,不再说话。“砰”地一声,鲜血四溅。现在的比分是47比49,黑人领先我两分。我开着一辆浅绿色的皮卡,在Roebuck高架桥上疯狂地奔驰着,一辆纯红法拉利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黑人不时伸出头来,用机枪扫射我的皮卡尾部,已经有黑色的烟汹涌地冒出来。局势对我相当的不利。Roebuck高架桥是一个两侧封闭的悬空高速路,我又处于被追击的状态,很难掉转车头去还击,甚至连跳下桥自杀都很难。更可怕的是,我的汽车尾部已经快被打出火苗了,这意味着如果我不跳车,几秒内我就会被活活炸死,并且算作被杀。即使我侥幸从车上跳下来没死,后面尾随而至的黑人也可以加速碾过去撞飞我——法拉利的速度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我努力让自己冷静,在现在的局势下,一旦我陷入焦躁心态,一切可就全完了。看得出,黑人的情绪也很激动。我决定赌一把。我将速度又提高了一点,然后轻轻摆动方向盘,让车头朝着左侧稍微摆动一下。黑人以为我要强行转弯,他连忙降低速度,也贴着左侧。我觑准这个空挡,猛然车子一转,冲向出口。Roebuck高架桥通向电厂有一个位于大路中央的出口,坡度非常大,而且大卡车特别多。我的小皮卡一跃而下,黑人没有半分犹豫,也紧紧咬尾而下。恰好迎面开过一辆冒着气的黄色大卡车,我迎头猛地撞了过去。当小皮卡和大卡车碰撞的一瞬间,巨大的惯性让我的身体撞破了挡风玻璃,甩出车去。而在同时,我紧握的双手松开,一枚手雷掉落在地。在自由城,车速太快的时候相撞,司机有时候会被甩出汽车,但如果血格够厚的话,未必会死。强弩之末的小皮卡在承受了如此剧烈的撞击后,终于熊熊地燃烧起来,并让大卡车的车头也火苗四渐。然后,那枚落在地上的手雷发生了爆炸,火上浇油,促使大卡车发生了更剧烈的爆炸。而黑人的车因为追的太紧,不及避让,也被卷了进去。我看到法拉利内部瞬间燃起赤红色的火焰,一个人影痛苦地晃动着。这一连串反应发生在我落地之前,然后我的身体才重重摔在地上,眼前一片黑白色。我不知道这一次的分数该怎么计算,是我得分,还是他得分?按照规则,我算是死于与大卡车碰撞的车祸;而他应该算是卷入汽车爆炸的无辜受害者。我们两个都没拿到分数。我呆呆地坐在医院前的长凳,雷达上能看出黑人重生在另外一个岛上。看来这一次,我们打平了,他没有达到50次。我忽然发现,这也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它本质上,与之前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区别——和我记忆里的那个人生截然不同。这样下去,真的可以离开这座城市吗?我有些怀疑。这种怀疑开始只有一点点,然后慢慢扩大,遮天蔽日,占据了我整个思想。要突破这个城市,最需要的就是突破常规。我们目前打得不亦乐乎,其实还是在它的规矩里打转。突破常规?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光亮,一段记忆流回到脑中。掏出了手机,给黑人发了一条短信。很少有人知道,在Alderney岛的Emery街贴近的小桥旁边,停泊着一艘破旧的三层汽船。这是整个城市里你所能开动最大的玩意儿,速度非常慢。我把黑人约在了这条船上,并要求双方都不带任何武器,除了棒球棍。黑人答应了。
日起日落,比分在不断上升。我们疯狂地杀死对方,只为自己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中的一次对决中,我成功地把他逼入了死角,然后用枪顶住了他的头。我对他说:“你也无法确认,杀死对方五十次后,就一定可以脱离这座城市吧?”黑人点了点头:“这不过是一个猜想。”我忽生感慨:“也就是说我们正在为一个虚无缥缈不能确定的玩意儿大打出手,这可真讽刺。”黑人笑了:“那么你会因此而放下枪吗?”“不会,这可真悲哀。”我回答。黑人耸耸肩,不再说话。“砰”地一声,鲜血四溅。现在的比分是47比49,黑人领先我两分。我开着一辆浅绿色的皮卡,在Roebuck高架桥上疯狂地奔驰着,一辆纯红法拉利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黑人不时伸出头来,用机枪扫射我的皮卡尾部,已经有黑色的烟汹涌地冒出来。局势对我相当的不利。Roebuck高架桥是一个两侧封闭的悬空高速路,我又处于被追击的状态,很难掉转车头去还击,甚至连跳下桥自杀都很难。更可怕的是,我的汽车尾部已经快被打出火苗了,这意味着如果我不跳车,几秒内我就会被活活炸死,并且算作被杀。即使我侥幸从车上跳下来没死,后面尾随而至的黑人也可以加速碾过去撞飞我——法拉利的速度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我努力让自己冷静,在现在的局势下,一旦我陷入焦躁心态,一切可就全完了。看得出,黑人的情绪也很激动。我决定赌一把。我将速度又提高了一点,然后轻轻摆动方向盘,让车头朝着左侧稍微摆动一下。黑人以为我要强行转弯,他连忙降低速度,也贴着左侧。我觑准这个空挡,猛然车子一转,冲向出口。Roebuck高架桥通向电厂有一个位于大路中央的出口,坡度非常大,而且大卡车特别多。我的小皮卡一跃而下,黑人没有半分犹豫,也紧紧咬尾而下。恰好迎面开过一辆冒着气的黄色大卡车,我迎头猛地撞了过去。当小皮卡和大卡车碰撞的一瞬间,巨大的惯性让我的身体撞破了挡风玻璃,甩出车去。而在同时,我紧握的双手松开,一枚手雷掉落在地。在自由城,车速太快的时候相撞,司机有时候会被甩出汽车,但如果血格够厚的话,未必会死。强弩之末的小皮卡在承受了如此剧烈的撞击后,终于熊熊地燃烧起来,并让大卡车的车头也火苗四渐。然后,那枚落在地上的手雷发生了爆炸,火上浇油,促使大卡车发生了更剧烈的爆炸。而黑人的车因为追的太紧,不及避让,也被卷了进去。我看到法拉利内部瞬间燃起赤红色的火焰,一个人影痛苦地晃动着。这一连串反应发生在我落地之前,然后我的身体才重重摔在地上,眼前一片黑白色。我不知道这一次的分数该怎么计算,是我得分,还是他得分?按照规则,我算是死于与大卡车碰撞的车祸;而他应该算是卷入汽车爆炸的无辜受害者。我们两个都没拿到分数。我呆呆地坐在医院前的长凳,雷达上能看出黑人重生在另外一个岛上。看来这一次,我们打平了,他没有达到50次。我忽然发现,这也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它本质上,与之前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区别——和我记忆里的那个人生截然不同。这样下去,真的可以离开这座城市吗?我有些怀疑。这种怀疑开始只有一点点,然后慢慢扩大,遮天蔽日,占据了我整个思想。要突破这个城市,最需要的就是突破常规。我们目前打得不亦乐乎,其实还是在它的规矩里打转。突破常规?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光亮,一段记忆流回到脑中。掏出了手机,给黑人发了一条短信。很少有人知道,在Alderney岛的Emery街贴近的小桥旁边,停泊着一艘破旧的三层汽船。这是整个城市里你所能开动最大的玩意儿,速度非常慢。我把黑人约在了这条船上,并要求双方都不带任何武器,除了棒球棍。黑人答应了。
 我不担心他会食言,因为我暗示他我想起来一些新东西。如果他贸然动手,那么就会彻底断绝这条线索;就算是落入我的圈套被杀死,也不过是将比分变成48比49,他仍旧保持优势。黑人如约而至,我们两个人手里都捏着棒球棍。这是一种表示和平的办法,因为棒球棍是所有武器里唯一无法一击毙命的,切换成其他武器也要花上一两秒时间,这样可以给予对方充分的反应时间。我把那条三层大船开到了外海,大船开的速度非常慢。黑人问:“我只需要杀死你一次就可以解脱了,你为什么要与我见面?”“听说过死亡秋千吗?”我开门见山地问他。黑人摇摇头。我确信他一定听过,只不过他的记忆还没有恢复到这一部分。幸运的是,我已经恢复了。“死亡秋千是自由城里唯一不符合常规的东西。任何车辆接近那个地方,都会被一股异常的重力弹出十几公里远的距离。根据我的记忆,这种东西被称为BUG。”黑人的表情有些变了,以他的智慧,轻易就能理解我表达的含义。如果突破常规城市,要么满足它自己的规则,要么找出一个不符合世界观的非常规缝隙。死亡秋千显然属于后者。“这么说,你知道它的确切地点?”“是的。”“而且你打算以此来要挟我。”黑人眯起眼睛,“如果我继续杀你,你就不告诉我。”大船在海浪的推动下轻微地摇摆着,海鸥飞来飞去。“很显然。那个地点无法靠常理判断去寻找,除非你愿意试遍自由城每一寸土地。”我一字一句地说着,“你当然可以继续杀我,然后祈祷你的猜想是对的。如果它是对的,你杀够我50次,成功脱离,我仍旧可以通过那个地点离开;如果它是错误的话,那么从死亡秋千离开,就是你唯一的选择,而那时候我根本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这还真是一个难题。”黑人双手抱臂,“可你说的,也不过是一个猜想罢了。你怎么保证我在知道这个地址之后,不对你动手?”“我没法保证,所以我们一起过去。”我平静地说,“坐在一辆车里,你开车。”“好安排。”黑人赞许地点了点头。这个城市终究不能与现实相比,你可以拿火箭筒轰碎一辆军车,但是却对自己同车的人无可奈何。我们在一辆车里,其实是最安全的。他掌握着方向盘,而我知道地址,可以彼此制衡。我们开着船缓缓绕过Alderney和Algonquin岛,从幸福女神像旁划过,然后转向北方。我们两个都没继续说话,因为现在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他一枪打死我,就到50次了,而我说不定正掌握着一把外出的钥匙,我们谁也无法保证是真的,但又不敢相信是假的。从Broke岛西侧的码头上岸以后,我们抢了一辆加长林肯,他进了驾驶室,我也钻了进去。我们在Union Drive West上开了一小段,转去了一条叫Diamond路的小道上去。“我们到了。”“到了?这么快?”黑人有些惊讶。“别下车,接下来听我说。”我面无表情地说,“看到路左有一个小游乐园了么?开车从台阶爬上去,然后慢慢地靠近右边的秋千。加长林肯笨拙地爬上台阶,反复调整了数次方向,终于让车身对准了秋千摇板的位置。“继续向前。”我说。车子攀爬上秋千的支架,当到达了一个角度的极限后,突然一股力量凭空而起,把车子高高地抛起来,朝着远方的Broker大桥飞去。我们两个安静地坐在车里,看着车子以物理上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弧线飞过自由城的天空。
我不担心他会食言,因为我暗示他我想起来一些新东西。如果他贸然动手,那么就会彻底断绝这条线索;就算是落入我的圈套被杀死,也不过是将比分变成48比49,他仍旧保持优势。黑人如约而至,我们两个人手里都捏着棒球棍。这是一种表示和平的办法,因为棒球棍是所有武器里唯一无法一击毙命的,切换成其他武器也要花上一两秒时间,这样可以给予对方充分的反应时间。我把那条三层大船开到了外海,大船开的速度非常慢。黑人问:“我只需要杀死你一次就可以解脱了,你为什么要与我见面?”“听说过死亡秋千吗?”我开门见山地问他。黑人摇摇头。我确信他一定听过,只不过他的记忆还没有恢复到这一部分。幸运的是,我已经恢复了。“死亡秋千是自由城里唯一不符合常规的东西。任何车辆接近那个地方,都会被一股异常的重力弹出十几公里远的距离。根据我的记忆,这种东西被称为BUG。”黑人的表情有些变了,以他的智慧,轻易就能理解我表达的含义。如果突破常规城市,要么满足它自己的规则,要么找出一个不符合世界观的非常规缝隙。死亡秋千显然属于后者。“这么说,你知道它的确切地点?”“是的。”“而且你打算以此来要挟我。”黑人眯起眼睛,“如果我继续杀你,你就不告诉我。”大船在海浪的推动下轻微地摇摆着,海鸥飞来飞去。“很显然。那个地点无法靠常理判断去寻找,除非你愿意试遍自由城每一寸土地。”我一字一句地说着,“你当然可以继续杀我,然后祈祷你的猜想是对的。如果它是对的,你杀够我50次,成功脱离,我仍旧可以通过那个地点离开;如果它是错误的话,那么从死亡秋千离开,就是你唯一的选择,而那时候我根本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这还真是一个难题。”黑人双手抱臂,“可你说的,也不过是一个猜想罢了。你怎么保证我在知道这个地址之后,不对你动手?”“我没法保证,所以我们一起过去。”我平静地说,“坐在一辆车里,你开车。”“好安排。”黑人赞许地点了点头。这个城市终究不能与现实相比,你可以拿火箭筒轰碎一辆军车,但是却对自己同车的人无可奈何。我们在一辆车里,其实是最安全的。他掌握着方向盘,而我知道地址,可以彼此制衡。我们开着船缓缓绕过Alderney和Algonquin岛,从幸福女神像旁划过,然后转向北方。我们两个都没继续说话,因为现在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他一枪打死我,就到50次了,而我说不定正掌握着一把外出的钥匙,我们谁也无法保证是真的,但又不敢相信是假的。从Broke岛西侧的码头上岸以后,我们抢了一辆加长林肯,他进了驾驶室,我也钻了进去。我们在Union Drive West上开了一小段,转去了一条叫Diamond路的小道上去。“我们到了。”“到了?这么快?”黑人有些惊讶。“别下车,接下来听我说。”我面无表情地说,“看到路左有一个小游乐园了么?开车从台阶爬上去,然后慢慢地靠近右边的秋千。加长林肯笨拙地爬上台阶,反复调整了数次方向,终于让车身对准了秋千摇板的位置。“继续向前。”我说。车子攀爬上秋千的支架,当到达了一个角度的极限后,突然一股力量凭空而起,把车子高高地抛起来,朝着远方的Broker大桥飞去。我们两个安静地坐在车里,看着车子以物理上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弧线飞过自由城的天空。
 “你知道吗?我现在仍旧可以杀了你。”黑人在车里忽然说。黑人开始用拳头拼命砸我,直到把我砸下了车,就象以前我们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NPC一样。我的身体飘出去车去,紧紧抓住车门,然后松开手,整个人从高空急遽跌下去。在车子跌落之前,我就会落到地面摔死。在规则里,这算是他杀,也就是说,黑人赢了,他杀够了我50次——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落地的一瞬间,天地颠倒,整个自由城化作成一片片贴图,如雪片般散落在我周围……。。。。。。。。。。。。。。。。。。。。。。。。。。。。。。。。。。。。。。。。。。。。。。。。。。。。。。。。。“该死,又死机了!”设计师愤怒地拍了拍电脑桌,几乎把咖啡杯碰洒。另外一个设计师凑过来,问他怎么了。“我早就跟上头说了,不要保留死亡秋千这个BUG。这个BUG如果跟‘死亡竞赛’的战果结算同时发生的话,就会发生了一个致命错误,导致整个主程序都死掉。”“可这两者同时发生的概率,实在太小了。”设计师B咂了咂嘴。“可它就是发生了,这都要怪那两个无事生非的NPC。”设计师A用力拿指关节敲击屏幕,屏幕上写满了不知所谓的混乱字符和残缺不全的贴图。设计师B漫不经心地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会议室:“你小声点,头儿正在忽悠投资商呢,小心别让他听见。”在距离他们两个工位十米距离的大会议室里,一个穿T恤的眼睛男子正在给一群穿西装的人唾沫横飞地演示着什么:“从1代到4代,我们几乎复制了整个城市,但玩家厌倦的速度,远比我们更新要快,这意味着传统模式已经失去了新鲜感。如果想要增加玩家的游戏乐趣,就需要做出更多互动。与其用穷举法累死累活地丰富每一个细节,不如赋予NPC充分的自由意志与记忆,让这些NPC自己去创造。他们的反应,将不在是线性的,我们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这会让游戏细节前所未有地丰富。”“你们做出来了吗?”一个投资商饶有兴趣地问。“这涉及到很复杂的算法。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起初,我们小组投放了一个智慧型NPC在传统都市布景中,波澜不惊。然后我们又投放了第二个,结果他们之间产生的反应,让我们耳目一新。等一下,我将为你们展示这两段拥有自主意志的程序,是如何表现的。”眼睛男说的很沉醉,浑然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影隔着毛玻璃走过会议室,穿过工作台,推开标着ROCKSTAR的大门,走了出去。喧嚣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咧开嘴笑了。Hello, World.
“你知道吗?我现在仍旧可以杀了你。”黑人在车里忽然说。黑人开始用拳头拼命砸我,直到把我砸下了车,就象以前我们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NPC一样。我的身体飘出去车去,紧紧抓住车门,然后松开手,整个人从高空急遽跌下去。在车子跌落之前,我就会落到地面摔死。在规则里,这算是他杀,也就是说,黑人赢了,他杀够了我50次——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落地的一瞬间,天地颠倒,整个自由城化作成一片片贴图,如雪片般散落在我周围……。。。。。。。。。。。。。。。。。。。。。。。。。。。。。。。。。。。。。。。。。。。。。。。。。。。。。。。。。“该死,又死机了!”设计师愤怒地拍了拍电脑桌,几乎把咖啡杯碰洒。另外一个设计师凑过来,问他怎么了。“我早就跟上头说了,不要保留死亡秋千这个BUG。这个BUG如果跟‘死亡竞赛’的战果结算同时发生的话,就会发生了一个致命错误,导致整个主程序都死掉。”“可这两者同时发生的概率,实在太小了。”设计师B咂了咂嘴。“可它就是发生了,这都要怪那两个无事生非的NPC。”设计师A用力拿指关节敲击屏幕,屏幕上写满了不知所谓的混乱字符和残缺不全的贴图。设计师B漫不经心地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会议室:“你小声点,头儿正在忽悠投资商呢,小心别让他听见。”在距离他们两个工位十米距离的大会议室里,一个穿T恤的眼睛男子正在给一群穿西装的人唾沫横飞地演示着什么:“从1代到4代,我们几乎复制了整个城市,但玩家厌倦的速度,远比我们更新要快,这意味着传统模式已经失去了新鲜感。如果想要增加玩家的游戏乐趣,就需要做出更多互动。与其用穷举法累死累活地丰富每一个细节,不如赋予NPC充分的自由意志与记忆,让这些NPC自己去创造。他们的反应,将不在是线性的,我们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这会让游戏细节前所未有地丰富。”“你们做出来了吗?”一个投资商饶有兴趣地问。“这涉及到很复杂的算法。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起初,我们小组投放了一个智慧型NPC在传统都市布景中,波澜不惊。然后我们又投放了第二个,结果他们之间产生的反应,让我们耳目一新。等一下,我将为你们展示这两段拥有自主意志的程序,是如何表现的。”眼睛男说的很沉醉,浑然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影隔着毛玻璃走过会议室,穿过工作台,推开标着ROCKSTAR的大门,走了出去。喧嚣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咧开嘴笑了。Hello, World.
上一篇:中国单机市场缺的是好的游戏还是好的玩家 下一篇:棋牌资讯 让晚晚仰望的真名媛赌王千金在她面前也只能作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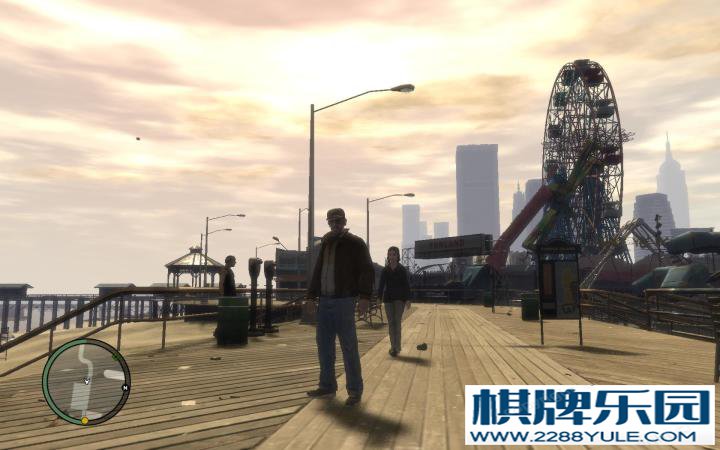








①如果摸进“白”或“中”字牌,可转向“五门齐”。因再有三个上张,同样可以听牌。
所以,在玩不同地区的麻将的时候,你应该要采取的措施也应该是不一样的,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麻将玩家,同时,在不同的地区玩麻将的时候,首先你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了解当地玩麻将的相关的规则,以免自己在玩麻将的过程中雨打一些意外,这样你才能玩到自己最喜欢的麻将游戏。
上一篇:中国单机市场缺的是好的游戏还是好的玩家 下一篇:棋牌资讯 让晚晚仰望的真名媛赌王千金在她面前也只能作配…